北大教授24小时照护失能母亲:未来独生子女处境更难
今年4月,产妇护理13825404095一篇“北大教授成24小时照护者”的文章刷屏,
文中主角胡泳今年50多岁,
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,
他的母亲今年85岁,
患有阿尔茨海默症3年,
胡泳也没有想到,
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母亲的“护工”。

▲
胡泳和保姆每天都要推母亲出去晒太阳
胡泳不得不削减在科研、学术上的时间,
每天六点半起床,
陪母亲吃饭,洗漱,晒太阳,
除了工作,大部分时候都在家里。
在重复的照护日常当中,
他也常在思考,
失去记忆的母亲究竟还是不是自己的母亲?
如果照护的结果必然失败,是否还有意义?
胡泳在朋友圈签名处写下里尔克的一句诗,
“有何胜利可言?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
从学者到照护者,
他如何看待照护和养老问题?
今年5月,
我们在北京拜访了他的家。
编辑:张雅兰
责编:倪楚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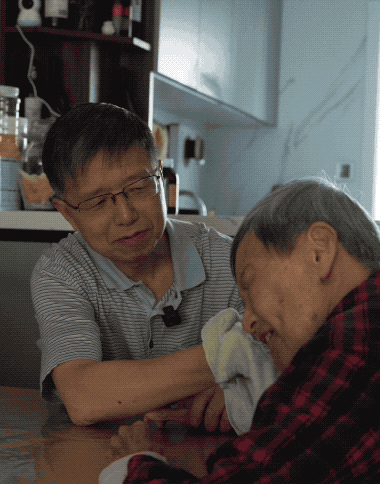
▲
胡泳给母亲擦脸、喂水
“人生始于屎尿屁,终于屎尿屁”,在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3年后,胡泳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当这位北大学者决定将自己作为照护者的经历发表出来,照护这个议题,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,照护者这个向来隐形且沉默的群体,也获得了更多关注。
我们见到胡泳时,他刚陪母亲吃完早饭。母亲眼前放着摊开的杂志,胡泳坐在一旁给母亲擦嘴、擦脸、喂水,母亲有时静默,有时则不耐烦地将胡泳推开。随后,他给母亲穿好衣服、和保姆一起将母亲扶上轮椅,推着母亲下楼晒太阳。这是每天固定且重复的日程。
胡泳将母亲推到楼下一片阴凉地,母亲怔怔地盯着前方,不言不语。胡泳坐在一旁,抽空回复一些工作消息。母亲表达已经不太清晰,胡泳还是能大概猜到她的心思,偶尔帮她折下路边一根野草,尽量满足她的需求。

▲
胡泳和母亲看着玩耍的孩子
在他们不远处,几个妈妈正围着一群3、4岁的孩子,他们叽叽喳喳地吵闹着,自顾自地跑来跑去。两幅场景形成对比,也恰好映照了胡泳近两年意识到的问题:人在生命两端都需要照顾,否则孩子会夭折,老人会被遗弃。照护是人生状态的一部分,应该上升到人的基本境况去认识。
“但是照顾孩子好歹满怀着希望,但是照护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,则一定意味着失败,所以这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。”
将母亲推回家里,胡泳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包,他要立刻赶到北大参加学生的毕业答辩。母亲的沟通能力严重退化,也常常不记得胡泳是谁,但最朴素的关心,依然存在于她的潜意识里,她总要问胡泳,“到点了?你这就走了?你有饭吃吗......”胡泳轻轻拍拍母亲的肩膀,“我有饭吃,你在家好好的,我下班就回来。”对胡泳来说,如今的生活大抵每天如此,很简单。

▲
胡泳为母亲摘下一株草,老人已经很难表达,两人只有这样简单的交流
作为他人眼中的高级知识分子,旁人下意识觉得,胡泳理应和更有价值的工作绑定,但尝到照护的苦楚后,胡泳觉得,照护的价值被轻视低估了,照护者需要外界的支持,社会的帮助。
中国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数量有4000多万,这也意味着有4000多万的家庭要面临照护难题,需要有人将这些经历摆上台面来讲,“如果你默认他人根本无法理解你,就等于掐断了最后向外界表达的机会。”
胡泳说,世界上只有四种人:曾经是照护者的人,现在是照护者的人,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,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。照护是每个人都终将面对的议题。
面对社会的老龄化趋势,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,下一代照护者或许将面临更加严苛的照护处境,胡泳希望,大家能更加开放地谈论疾病、衰老和死亡,更新固有的认知,从符合人性的角度出发,让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成为可能,也给予照护者更多支持,被照护者更多尊严。
在刚刚开始照护父母之后,胡泳曾在朋友圈签名处写下了里尔克的一句诗,“有何胜利可言,挺住意味着一切。”在“挺住”背后,他从没有丧失意义感,也向内求得了更多关于生命的答案。
以下是胡泳的讲述:


▲
胡泳和保姆扶母亲上轮椅
我是60年代生人,现在在北大教书,快退休了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时间比较长,但之前他们身体一直很正常,但到了某个时刻,你发现自己突然进入了照护阶段。3年前,我母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,去年,我父亲去世了。
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,晚上12点睡觉。偶尔参加一些公共活动,其余时间基本就呆在家里,生活挺简单的。因为我妈现在饭吃得很少,所以我们也改成一天吃两顿了,我负责买菜,保姆来做。
我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,但因为我姐姐不在北京,所以目前主要是我和我哥分工照顾。但因为我母亲住在我家里,我就成了主要的照护者。疫情的时候,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。因为当时我还要照顾我父亲,还要避免他们被传染,我当时真是筋疲力尽了。
我妈妈的记忆力、语言表达都在急剧退化,我有很多杂志,我偶尔会教她一些里面的字,像教小朋友一样。大部分时候,她会假装在看杂志,我也不理解她说的话,只能猜。

▲
照料完母亲,胡泳要立刻收拾东西赶往学校工作
之前很多人问我每天在照护上花多少时间,因为我们平常做事,会按照时间的团块来决定做什么。但照护就会将你所有的生活全部打乱,你没法计算时间。
照护的日常是语言难以描述的。有时候我觉得很委屈,我是为你好,但你不领情,明明已经为你牺牲了这么多,你还是对我想骂就骂。有时候已经很累了,但她就是不睡觉,或者一直在收拾东西,把所有东西摔一地,夜深人静大声嚷嚷,就是要跟你反着来,这些时刻都会让人失控。

▲
胡泳和父母合影
我有时候觉得命运像一个开玩笑的人,我妈以前是非常开朗的,是个有名的大嗓门儿,现在极其安静。她在逐渐变老的过程里,也变得很窝囊。以前她是非常利索的一个人,家里洗洗涮涮,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。现在她由于没有排便意识,会让家里常年弥漫屎尿味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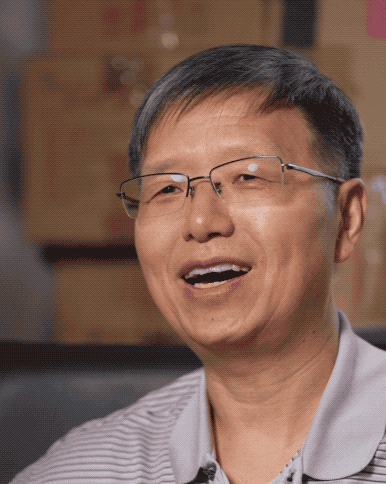
▲
谈起母亲,胡泳眼眶湿润
大家都不是圣人,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冲她嚷嚷,我哥我姐也会。但事后我又会很内疚,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,就像是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生气。
我也会有破防的时候。当我妈第一次特别正经严肃地问我,你妈妈好不好?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还有一次我姐从外地过来,我妈妈刚开始都不记得我姐了,她问,你来了?那你妈妈在家谁管?我姐当时就崩溃了。这样的时刻太多了。


之前我写了一篇谈照护的文章,引起大家的讨论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或者原因,每年一批新生成为我的学生后,会有一个“胡门第一课”,就是大家见面吃饭聊天,我也会提前征集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聊一聊,当时非常意外,有学生提到想听听照护这个话题。

▲
胡泳和学生
这一代的孩子都是00后,他们的父母开始照顾他们的祖父母,对他们来说,照护还是相对遥远的。我讲完之后,他们才意识到了原来父母那么辛苦,也会担心自己未来的照护问题,老了谁来照顾自己?
网络上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反应,他们觉得,北大教授应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,而不应该将时间花在这件事(照护)上。还有些人觉得北大教授的生活条件可能比一般人好,他都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,那普通人怎么办?
还有些人没仔细看文章,下意识觉得我是女性。我们生活在男权社会,男性相对有权势,女性没有。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把育儿、照护这些事甩给女性去做,这个工作也被认为是相对没有价值的。
大家的逻辑也是如此,我是一个大学教授,似乎就应该干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,而照护是一个低级的工作。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。你的工作的价值就一定那么高吗?你的妈妈处于失智的状态,你和她在一起,价值有那么低吗?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,就能解决一些纠结挣扎的问题。

当我说出自己的经历后,很多曾过照护经验的人,觉得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。其实大家都觉得,就算说出来,别人连十分之一都理解不了。但我觉得照护还是应该公开讨论的,因为照护者面临着巨大压力,也需要社会的帮助。
照护其实是我们人生状态的一部分。在生命的很多阶段,你都能找到相似的部分,比如之前就有妈妈留言说,这不就跟带孩子一样吗?人最独特的地方,就在于人在生命的两端都需要别人照顾,因为如果没人照顾,小孩会夭折,老人会被遗弃。
从这个角度讲,生命前端的养育和后期的照护都证明了人本质上的脆弱性,不管你曾经有多厉害,叱咤风云,身强体健,只要到了一定的阶段,都需要别人照顾。
很多人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也不足。我母亲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记忆的丧失,她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,白天当黑夜,反复地收拾东西。很多人可能就会说,老人上了年纪了,记忆力不好,忘性大了,一句“老糊涂了”就带过了,大家会有回避。
对于疾病和照护,很多人不了解,这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我觉得有必要将照护这件事上升到人的基本境况来认识。

▲
江边的老人(与文中人物无关)
我其实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。我正好面临着养育和照护两方面的压力,我现在工作量还是挺大的,两个孩子也还没有成年,压力很大。
其实正常来讲,你的伴侣才是第一顺位,孩子排第二,其次才是父母。但由于目前我母亲这样的状况,我只能寻求我的伴侣、孩子的谅解。我每年只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能陪伴他们,我一直在各种内疚里面挣扎。
照护不是个人的事情,它一定是一个家庭的事。所以你不能只考虑你自己的想法,大包大揽。我公开谈论我的经历,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避讳谈论疾病和死亡。中国家庭有一个基本的运作模式,就是大家从来不把话当面说清楚,每个人还都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,最后不光会产生矛盾,还可能反目成仇。
所以我觉得,如果一个家庭进入了照护阶段,全家人一定要坐下来,将这些事放在桌面上讨论。如果父母还意识清醒,也要让父母提前参与到这个过程中,可能父母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,大家要提前说清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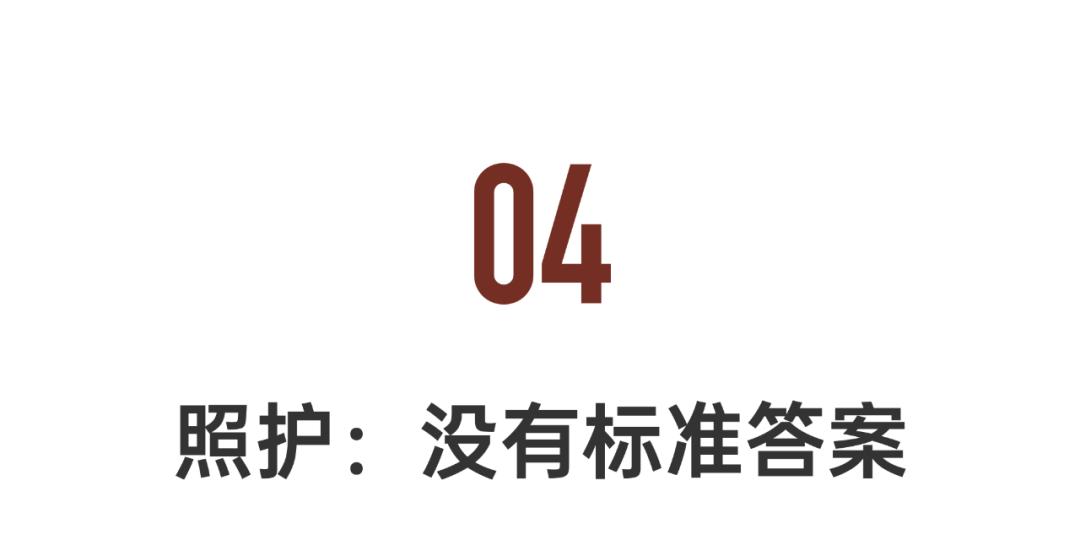

之前我收到很多留言,大家都问为什么不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,让专业的人来帮助你。也有些人说,只有在家里,老人才是最舒服的。
其实我当时考虑过将母亲送到养老院,甚至全家出动去考察,但是我妈妈明确表达了不愿意,我当时就把这个动议彻底废除了。
我觉得如果能让老人自己选择, 百分之九十的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。因为和老人尊严最相关的东西,叫独立自主性。人进入老年后一个非常大的恐慌,就是丧失了独立自主,比如生病了,必须要坐轮椅,自己没有多大的反抗能力,就必须听从子女的安排。
在养老院,人不可能有独立自主性的,因为它是机构,你周围都是陌生人,你也必须按这个机构的规定来,会对你产生各种限制。
从符合人性的角度来讲,人应该居家养老。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,这并不现实。
在过去的中国,基本是家族式养老,所以不太构成问题,但是我们不能罔顾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。
由于人口的流动性,现在传统家庭的规模缩小了,很多子女和父母不在同一个城市,老人也没有那么多子女,因此未来独生子女一代长大后,可能会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。
我觉得,未来的养老应该多在社区上下功夫,让很多问题交给社区来解决。比如,可以建立更好的社区卫生中心,让每个社区都能开食堂,这样老人就不用在家里做饭了。也可以在社区开一些托老所,早上把老人送过去,晚上接回来。
还要强调一点,虽然我自己没有选择养老院,不代表我建议大家都不要选择养老院,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状况来决定。事实上,只要进入衰老这个过程,就没法有两全其美的选项。关于照护,没有标准答案,是因人而异,因家庭而异的,要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作衡量。

很多人也说,如果连生活在大城市的老人依然面临照护困难,很多在农村里生活的老人可能处境更难。我母亲以前在农场工作,她是农场工人,所以她也没有养老保险,退休金只有很可怜的一点钱。我觉得,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。


▲
胡泳毕业时和父母合影
我是一个很难丧失意义感的人,从小到大,无论做什么事,我都觉得不徒劳。我既是父母,也是我父母的孩子,做好父母是你人生的一部分,你有义务和责任,反过来,照顾父母也是一样,这些都构成了你必须要做的事情,所以它肯定是有意义的。
但是我干的这个事是一件注定失败的事,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成功。这跟带孩子还是有很大差别,带孩子还是能看到希望的,有一种期望会激励着你,但照护这件事的结局就是失败,所以必然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。
但是我已经将这件事想清楚了,当时我照顾我父亲去世,做临终关怀、订立遗嘱、举行告别仪式,最后将我父亲埋在长城脚下,作为儿子,我都尽力了,所以最后我的心情很平静。

▲
在学校讲课的胡泳
以前我是到处飞的,参加国内国外各种学术研讨,写书、上课,但是我觉得生命本身在早期,它是向外扩张的,努力找更大的世界,但是到了一定阶段,就会变成内敛,你要收回来,但收回来也不等于你的世界就因此缩小,内心世界完全可以像外部世界一样辽阔。
很多人在进入照护的时候,把这看作一种风险、威胁和厄运,我觉得要善用这样的机会,它真的是很好的提升自己心灵丰富性的机会。

▲
电影《妈妈!》,讲述了女儿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故事
其实在照顾我母亲的过程当中,我也衍生了很多其他思考。如果我母亲失去了所有的记忆,她在什么程度上还是我妈?
我一边想,一边思考AI的问题,大家也一直争论,AI是否会取代人。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前景是用人工智能来替代人,叫做“接管”。大家普遍认为,人工智能要有人类的意识,大脑比较重要,身体不重要。
但我认为身体极其重要,在意识上,我妈不是我妈了,但在身体上她绝对是。现在我在辅助她的时候,我能清楚地想起以前和她接触时的所有气息。所以我现在比较坚定,人工智能如果没有身体,它就不是人。
此外,我觉得环境很重要,我们当然可以造一个人工智能来代替人,但是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环境里的。是我们和周围的环境、各种人都发生交集后,这些东西共同组成了我的生活。所以人工智能复制的人的意识,不能复制人的境况和周围的环境,就不能真的取代人。
所以我认为,思考照护,本质上是在思考哲学问题,最终都回到了你是谁的问题。某种层面上,这也让我从目前的日常中,找到了一些安慰和解脱。未来,我也希望能将这段经历写下来,更深入地研究阿尔茨海默症这种疾病。